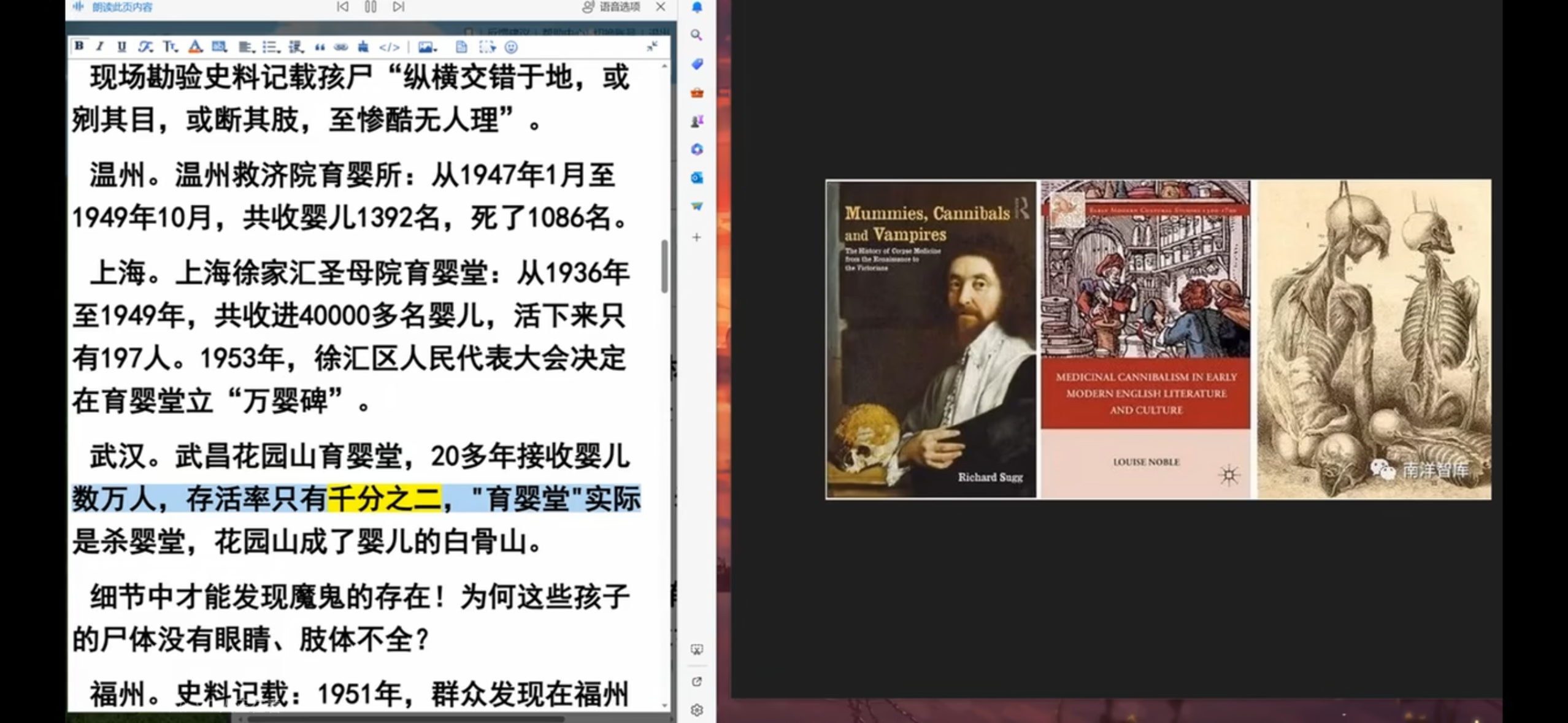想象一下,你漫步在17世纪伦敦的药房街区,空气中混杂着没药、肉桂与一丝隐约的腐甜。柜台上,一瓶标着「Mummy」的深色粉末静静陈列,售价不菲。店员郑重推荐:这可是上等货色,能治瘀血、止痛、甚至延年益寿。你或许会皱眉,却也见惯不惊——因为在那个时代,吃人,并不是野蛮部落的专利,而是欧洲上流社会最时髦的医疗秘方。这段被历史有意遗忘的篇章,如今由两位学者的著作重新揭开:路易丝·诺布尔(Louise Noble)的《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与文化中的食人医疗》(2011),以及理查德·萨格(Richard Sugg)的《木乃伊、食人族和吸血鬼:从文艺复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尸体入药史》(2011年初版,2015年再版)。这两本书并非同一部作品的译本或改编,而是各自独立的学术巨制,却因主题高度重合,常被并置讨论。它们共同告诉我们:欧洲人一边谴责「野蛮人」的食人,一边在自家药柜里珍藏着同类的残躯。
🫀 人体即药柜:一场横跨六世纪的医疗狂想
让我们先把时间拉回16世纪。埃及木乃伊被成批运到欧洲港口,药剂师们将其磨成粉,命名为「mummy」。最初,这词指从波斯山中渗出的天然沥青,因其防腐特性而被视为万能药。后来,供不应求,欧洲人干脆「就地取材」:刚被绞死的罪犯、战场上阵亡的年轻士兵,甚至意外身亡的健康青年,都成了原料。尸体被迅速处理——抽血、取脂、剔骨、风干——制成油膏、粉末、酊剂,堂而皇之进入皇家药典。
什么是「mummy」?
在早期现代英语中,「mummy」一词经历了奇妙演变。最初指天然沥青(bitumen),因其黑色黏稠、能防腐而被阿拉伯医师推崇。中世纪后期,欧洲人误以为埃及木乃伊就是用这种沥青浸泡而成,于是直接把木乃伊本身当作药材。到16-17世纪,「mummy」已泛指任何干燥的人体组织,尤其是头骨粉与脂肪。药剂师相信,年轻、暴毙者的尸体含有最充沛的「生命精气」,能传递给病人。
这种信仰并非民间迷信,而是得到当时顶尖智者的背书。化学医学的先驱帕拉塞尔苏斯(Paracelsus)主张「以人治人」;弗朗西斯·培根、罗伯特·波义耳这些科学革命的旗手,都在笔记或处方中留下人体药材的记录。甚至查理二世据说亲自在宫廷实验室提炼「国王之滴」(King』s Drops)——用人类头骨蒸馏的酒精酊剂,用来治疗他的癫痫。
🩸 莎士比亚的药方:文学如何吞下真实的血肉
路易丝·诺布尔把镜头对准英国文学。她发现,莎士比亚、斯宾塞、多恩这些巨匠的笔下,频频出现「mummy」的影子,却绝非偶然的异国情调,而是日常医疗现实的折射。在《奥赛罗》中,那块「用少女心血浸染的 mummy」手帕,既是爱情信物,又是疗伤圣物;在约翰·多恩的宗教沉思里,吞噬基督的身体(圣餐)与吞噬死者的身体(药用)形成诡异的平行。诺布尔指出:圣餐礼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食人——「这是我的身体,吃吧」——它为欧洲人提供了心理缓冲,让他们在药瓶前不必太过道德焦虑。
圣餐与食人的心理桥梁
基督教核心仪式要求信徒「吃基督的身体、喝基督的血」,这在字面意义上就是食人象征。早期现代欧洲人正是在这一神学框架下,合理化了自己的尸体医学: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吞噬神子,为什么不能吞噬凡人?这种矛盾让他们在谴责美洲原住民「野蛮食人」的同时,安心服用从绞刑架下抢来的新鲜血液。
诺布尔进一步挖掘:文学中的食人意象,往往承载着殖民焦虑。欧洲探险家在旅行记里渲染新大陆的食人部落,却闭口不谈自家药房的木乃伊粉。这种双标,恰恰映照出文明与野蛮的界限是如何被随意移动的。诺布尔用细腻的文本分析告诉我们:身体不是单纯的肉体,而是意义的容器——被吃掉的身体,意味着力量、纯洁、甚至永生的转移。
🧪 从绞刑架到战场:萨格笔下的欧洲「吸血鬼」日常
如果说诺布尔聚焦英伦岛国的文学镜像,理查德·萨格则把地图铺开到整个欧洲,甚至延伸到维多利亚时代。他的书厚达456页,像一部尸体医学的百科全书。从意大利的蒸馏实验室,到德国的行刑场,再到爱尔兰战场的「脂肪收割」,萨格用大量原始档案重建了供应链:刽子手在绞刑后立即放血,围观的药剂商举着瓶子接;战场上,士兵们趁尸身未寒,割取脂肪制成油膏。
萨格最震撼的论点是:尸体医学的高峰,恰好与欧洲科学革命重合。理性时代的巨人——波义耳、牛顿、哈维——并非彻底抛弃「魔法」,反而在实验室里延续着古老的活力论。他们相信,人体携带着某种「精气」(spiritus vitalis),必须从鲜活来源获取。萨格还延伸到文学:布拉姆·斯托克笔下的德古拉伯爵,饮人血以永生,原型正是现实中那些贵族与科学家偷偷服用的「新鲜人血疗法」。
第二版新增了北欧的「饮血仪式」、用人脂制烛的巫术记录,甚至人皮手套的案例。萨格用黑色幽默写道:真正的吸血鬼不是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,而是伦敦药房的绅士们。
🔍 两书交辉:文学的隐喻与历史的血迹
尽管侧重不同,两位作者在核心悖论上惊人地一致:欧洲基督教文化如何在「不可食人」的禁忌与日常医疗实践之间维持平衡?答案都指向圣餐礼——它让「吃人」变得神圣而抽象,从而为现实中的尸体药材提供了文化护照。
诺布尔的书更像一柄手术刀,精准解剖文学文本中的象征网络;萨格的书则像一幅全景地图,标注了从文艺复兴到维多利亚的每一处「采血点」。前者242页,精炼优雅;后者456页,材料浩繁。评论家常将两者并置:诺布尔照亮了文化想象的幽暗角落,萨格则提供了坚实的史实骨架。它们共同颠覆了一个线性进步史观——我们并非从「迷信」径直走向「理性」,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把魔法与科学搅拌在同一只坩埚里。
🩺 余音:从木乃伊粉到器官移植
当我们合上这两本书,会发现历史的回声仍在回荡。今天,我们谴责非法器官交易,却在自愿捐献体系中延续着「以身体救身体」的逻辑;我们震惊于过去的尸体医学,却忘记现代医学同样建立在解剖与移植之上。诺布尔与萨格提醒我们:身体从来不是纯粹的物质,而是承载欲望、恐惧与希望的符号。欧洲人曾经在药瓶里寻找永生,如今我们在冷冻舱与干细胞里继续追寻。区别只在于,我们学会了用更体面的语言包装同样的冲动。
两本书的出版年份同为2011年,仿佛历史在那一刻集体失语后,又同时开口。它们不是互相抄袭,而是同一股学术暗流的双生浪花。今天,当我们回顾这段「被遗忘的食人史」,会发现最诡异的不是那些粉末与酊剂,而是人类对自身身体永不餍足的渴望——我们害怕死亡,所以愿意吞噬死亡本身。
参考文献
- Noble, Louise. Medicinal Cannibalism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. New York: Palgrave Macmillan, 2011.
- Sugg, Richard. Mummies, Cannibals and Vampires: The History of Corpse Medicin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Victorians. London: Routledge, 2011 (2nd ed. 2015).
- Paster, Gail Kern. Review of Medicinal Cannibalism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y Louise Noble. Renaissance Quarterly, 2012.
- Henry, John. Review of Mummies, Cannibals and Vampires by Richard Sugg. Times Higher Education, 2011.
- Jacobson, Miriam. Joint review of Noble and Sugg』s works.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, 2013.